村口的老人窃窃私语,说老年机里面有黄金
五月是种花生的季节,不然就晚了。白天,桃园人都在外面的地里撒种。干活时顾不得,一旦闲下来,就各自找个舒服的角落蹲着,像个工作似的扒拉手机。
这是山东半岛东南部丘陵地带的村庄。留守于此的人与千亩田地、百亩林场、昼夜播放的短视频生活在一起。

土地里种着玉米、小麦、花生。高高的坡上可以看到风力发电机,像立于远山的巨人 | 作者供图
永奶奶
永奶奶一起床就看手机、上抖音,烧火时看,吃饭时也看。干活时,她盘腿坐在炕头,裁童男童女的衣服,微胖的上半身靠着略显单薄的下肢。手机放在被褥上,屏幕一刻也没有暗下去。
看得火苗窜到灶台上,衣服差点裁错。心思不在眼前,一餐啃口馒头就匆匆完事。
她提笔忘字,有时候给别人评论,忽然忘记哪个字怎么写,就趁着火还没烧出来,跑到隔壁找人问。
睡前必须划拉几下,起夜方便回来,也要打开抖音。外放的声音把老伴都吵醒,气气囔囔地再睡过去。
“长在抖音里了,进去那个世界里了。”用村里人的话讲是。
永奶奶的智能机是去年 1 月在镇上花 1000 多元买的。买来了,不会用,放在抽屉里发愁。想起来就给它充个电,像养了只宠物。小姑子笑她,“劝你买智能机是为了让你潇洒潇洒,不玩抖音白活了。”
老太太一下子精神起来,摸索着学习,遇到不会的地方,就请教孙女、邻居和朋友。她觉得自己“一点就通”,很是骄傲。大侄子还帮她下软件,教她怎么剪视频传到抖音里。买了专门拍视频的伸缩支架,像盏落地灯,在卧室门口直挺挺立着。
自此,玩抖音便成为永奶奶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件事。
拍乡间的花草,劳作的场景。
拍自己组织的舞蹈队跳舞。
拍滤镜下变年轻的自己:“多好看啊,看不腻。”
拍对口型的音乐视频,跟着抖音现学现卖,也拍自己清唱的老旧情歌。她的嗓音高亢、洪亮,每句都拉着长长的尾音。小儿子说她唱得不好听,但她满不在乎。
以前她不敢唱。
“那个旧社会不得了。”年轻时她就喜欢唱歌。婶婆来家里闲聊,老远听到有人唱,进屋见到她还笑嘻嘻的,便以为她得了神经病。“我问她你来做什么,她说我来看‘超霸’。她是以为我傻了。”后来,她就只在被窝里小声唱。

永奶奶的抖音 | 作者供图
她在桃园住了二十多年,再往前是在大寨,遇到了现在的老伴。20 岁结婚,做保健员,当幼师,卖衣服,“稀里糊涂生了三个孩子”。背着孩子拉大锯,身子往前倾,孩子就往前倾,往后仰,孩子也就跟着往后仰。
日子紧张,地里的柴火都要被集体收了去,只能捡点玉米叶子烧火。走几里地担地瓜回来,发现年幼的孩子独自睡倒在大水缸边,惊出一身汗。“那些年分工分,自己只吃到了那点累。”
家庭的劳累,时代的保守,这些限制终于随着生命的前进而消退。 73 岁的她,一心扎到了手机里。
永奶奶已经发了 6000 多个视频。最多一天发 20 个,少的也有三四个。要根据当天穿的衣服来数才记得清。再多也不敢发了,觉得占用别人发抖音的机会。
偶尔她也拉着老伴拍,自编自导小品,在卧室的背景里一问一答。老伴有时不情不愿,但她觉得,“能让你上抖音,你应该感到自豪呢”。
在她心里,上抖音就是“潇洒”,是让自己高兴。生活中也有不快乐,但一玩抖音,什么糟心事都忘掉了。“必须是我喜欢的模板,我喜欢的歌。除此之外,我不发。反正也是玩,就是高兴,感到心里痛快。”

卧室一角。西墙边摆着电视,没有开,后面塞着一堆纸和写满 Wi-Fi 账号和密码的盒子 | 作者供图
6 片叶子和 12 片叶子的庄稼
“跟社会”是村里老年人中极普遍的一种心理。智能机,代表一种更被周围人认可的身份地位,区别于那些落后的人。
女人一个字不识,是彻底的文盲。别人帮她把联系人输到通讯录里,告诉她怎么念,她就一遍遍地回顾,用脑子记下来。脑子有时不顶用,两个人名完全念错了。
虽然如此,她还是有一块智能手机。之前是老年机,但觉得“好不容易活一回人”,也想用用智能机。
王玉过去不懂这些。换成智能机之后,再回头看到那些用老年机的人,就看不惯了。玩抖音也是一样的,玩的人比不玩的人看上去更灵活,更跟社会。“有时候你发个视频,有人说,还用抖音,真浪啊。我就会想,我也不碍着你,而且我会用抖音,你不会。”
去城里的诊所找熟人针灸,她会故意把手机拿出来,打开抖音看看,也给那个大夫看。
“显摆我会玩,有智能机。”
上传视频也是为了显摆,向别人显摆自己的家是四间大屋。“如果外人不来我家,根本不知道我家什么样子,我把家拍出来给别人看看,别人就知道了,也会觉得,这谁家过得不错啊。我向别人显摆我会跳舞,会这个那个,也是想让别人认可我,夸夸我,对我有个印象。”
很久不上抖音,都不行,怕被别人忘记。
上抖音之前要把家里打扫干净,准备好衣服和首饰。

村民抖音页面 | 作者供图
“年轻的时候想让别人看自己,就很愿意出门,站到人眼前。没穿好衣服就躲着别人,怕别人笑话。”
有好衣服,就想拍个全身,没有就拍半身。冬天的衣服不够好看,就只拍脸;夏天有好衣服,就多拍。不仅身上穿得鲜艳,还要把最喜欢的几套都挂起来,做视频的背景。
王玉讨厌市面上的中年人款式,觉得显老,喜欢年轻、亮色的裙子。家里衣服多到放不下,每次拍抖音前都需要花很久捯饬。
玩抖音耗电多,新手机不舍得用,总是旧的、最不心疼的手机被用来专门玩抖音。于是村子里还形成了一个二手机流转的网络。
抖音上的专家说,玉米长出 6 片以上的叶子就得打抑制生长的药,不玩抖音的说 12 片叶子以上才打。玩抖音的和不玩的聊不到一块去,再聊下去就会伤害面子。

永奶奶观看的“金牌知识”主播 | 作者供图
老年机里的黄金
被淘汰掉的老年机,可以换回一个脸盆。
西茂财沟距永奶奶所在的桃园街道有三公里,进入村子前需要经过长长的公路,两边是耕地,整个村子像被包裹在树林里。地势高,布局略显杂乱,有的居民住在高台上,有的住在平坦的地面。
西茂财沟村口,两个老人坐在树荫下讨论:老年机里有黄金,大概有 1 克,回收旧手机就是为了把里面的黄金抠出来,铸成金块——“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该卖掉,应该自己把黄金找出来。”
老年机有巨大的键盘,有的镶了金边,顶部有两个手电筒。来电的时候轰隆隆震天响,常给身边人吓一激灵。智能机则像个神秘的精灵。
村里 79 岁的奶奶秀芬已经玩得很熟练了。前天晚上睡不着,她就摸起手机玩会儿,刷着刷着没电了,充满电后,无论怎么扒拉也不出声。她便拿起苍蝇拍的棍儿,敲打敲打,还是不管用,“不说话,变哑巴了。看了一晚上哑巴手机。”
“藏金子”一类的解释来源不明,在村子里口耳相传地长出了好多个版本。

乡下的手机店、宽带店(宽带店也卖手机)。它们的存在十分重要,除了挣钱,还要帮老年人解决各样琐碎的手机问题 | 作者供图
看抖音时间久了,两眼发黑,看不清人的样子。看电视上讲,正常情况下人一分钟眨眼 20 次,看抖音一分钟只眨一次。他们就说,因为看抖音的时候人被视频吸进去了,投入进去了。
他们也逐渐摸索出如何利用智能机赚更多的钱。秀芬发掘出快手极速版内好几个刷金币的功能,包括开宝箱、刷广告、在软件里“逛街”和“吃饭”,每天能赚 3 毛钱。
全村人都如火如荼地投入到刷视频赚钱的行列中。软件使用时间动辄十几小时,睡觉也要开着,插着充电,摊在枕边,滚动地划拉视频。他们总结出一些赚钱妙计:要综合多个软件;也要周期性地卸载再安装,不然会越赚越少。
村里收废品的管爷爷去年冬天开始已经挣了 300 多,目前是一分钟 1 毛钱。他说,再少一点,就要把它卸了,过几天再安回来,往复循环。
几毛几毛攒出来的都用来充话费,买一些日用品。“以前摘果子挣工分,现在刷视频挣分钱。”秀芬说,这是一样的事情。

村民发的抖音大多习惯加上字幕 | 作者供图
以路由器为圆心
今年,西茂财沟大队办公室里新设了一个无线网络。大队办公室位于村口。负责看守路口的孙午成率先连上了这个网络。
很快,他将账号密码分享给了负责清扫道路的王玉。闲暇时候,他们便坐在不远的树荫下歇息,偶尔打开手机看看。
直通村口的主路旁有个小水库,村口的位置在水库北侧,被人们叫做河坝的尾巴。晌午时分,孙午成就蹲坐在这里连网看手机,离大队办公室仅有十几步的距离。
路过的秀芬看到孙午成坐在河坝尾巴,好奇他在干什么。孙午成说,这里可以连网,不需要用流量,到南边就接收不到网络信号。王玉也附和,“差一点点距离就连不上网了。”
家里安装宽带网络在桃园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每一个接入宽带的无线路由器都是一个圆心,向外辐射出去,为蹭网的人们划定了可移动的范围,改变了日常行动的轨迹。
空旷的地方信号不好,经常需要等待加载。一旦加载好,短视频音乐就轰轰烈烈地炸出来。大家外放的声音都不小,多个伴奏混在一个空间里,大家却相互都不介意。
从前,闲下来的人们喜欢到街坊朋友家喝茶水,坐在屋山头聊天。如今这样的场面大为减少,只剩那些没有智能机或不玩抖音的坐在一起闲聊。

桃园片区,人们的一天从 5 点半开始,晚上7点半路灯亮起,店铺陆续关门,摊贩收拾回家 | 作者供图
因为出殡或者结婚的事聚在一起,也是各看各的抖音。彼此之间很少聊天,你跟对方聊,她会来一句“啊?”刚刚你说的话她根本就没听到。
男人的电视和女人的抖音
电视是不看了,也不知坏了没有。但大部分家庭里,它仍占据客厅正中间的位置,周末的时候小孩子会打开看一会儿动画片,“烧一烧”。
再往前的家庭设备是录音机,结婚时必备的四大件之一。
百花姨刚 50 岁,热情爽朗,有一副略微沙哑的嗓子,圆圆的脸蛋常常挂满笑容。染着一头红棕色的头发,白发依稀藏在其中。她平时最主要的任务是看店,最近,开始嚷嚷着要减肥,经常吃完晚饭从桃园街道散步到两三公里的地方,再走回来。
她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结婚时买的录音机:长条形,配有两个喇叭以及天线,播放时会闪不同颜色的光亮,两个喇叭可以折叠到顶部。
当单独问百花姨和她丈夫“家里录音机是否还留着”的时候,他们给了不同的答案。她丈夫说应该还放在某个犄角旮沓里,平时不拿出来听;百花姨却说,早在翻盖新房的时候,把以前的破烂物件扔掉了。
这不是个例。当问起家里的某个物件,甚至村里某个去世多年的人,男人往往只有个模模糊糊的印象,还以为对方活着。女人则更清楚实际的情况。
桃园的多数女性遵守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角色安排,妇女口中也常把丈夫称为“当家的”——女性对家庭事务了解更多,但却不代表她们拥有更多的家庭权力。
百花姨家里,丈夫掌管着电视的观看权。丈夫喜欢看战争片,看《亮剑》。而她自己喜欢古装剧。两口子之间需要有人让步,她说。女人们大多都这样说。慢慢地,在桃园,电视就成为了“男人的电视”。
但抖音是女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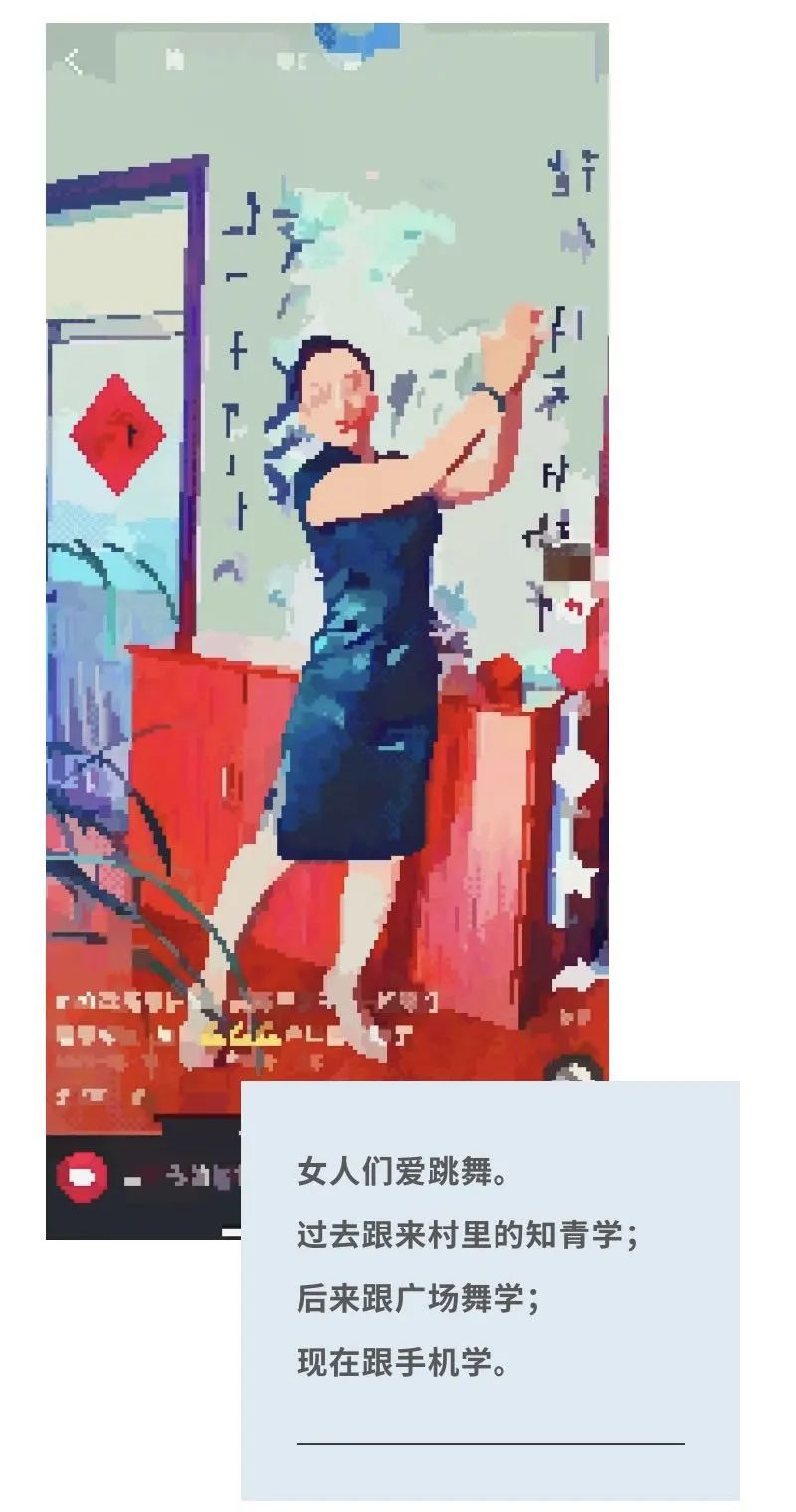
跳舞的视频 | 作者供图
男人大多觉得抖音是女人玩的东西,拍视频显得“娘里娘气”。在桃园,女性发抖音的概率更大,频率更高,在欢笑声中跳舞,对口型唱歌;相比之下,大部分男性用户处在静默状态——“只看不发”。因为这种差别,一些家庭里,男人还挎着老年机,而女人则已经用上了智能机。
乡村的传统观念认为女性不应该抛头露面,让人观看是不好的。外加抖音里的世界“很乱”,容易受人指指点点,所以起初,百花姨的丈夫不希望她上抖音(将自己的形象上传到抖音)。
百花姨则认为抖音很好,可以让她了解外面的世界,看不同地方的人都在做什么。在抖音上,她看人卖货,也看亲戚朋友、小学同学的动态。她还关注了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一个用户,天天看人放羊。
这种表达随着状态起伏,一阵一阵的。“有时候很想拍,心情好的时候看到喜欢的歌曲,寻思拍个视频吧;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就觉得,有什么意思啊。”

村民拍的抖音,广场舞的场景 | 作者供图
南海
软件上的互动像一种游戏,带着特效和气泡。但游戏规则仍被乡土社会的结构规训着。
“互关互评互赞”这一原则渗透到大多数人的观念和行为中,是礼尚往来的线上复现。不遵循的人会被认为是人品不行,不好交往。
王玉非常看重点赞量。每当好友给自己点一个赞,她会双倍回馈别人;相反,自己给别人点一个赞,别人却只回馈了一个,或者给别人点赞,别人却回复了一个评论——这种刚刚对等或不对等的行为在王玉心里均属小气。
视频流有同城和推荐两个选项,多数人更爱泡在同城里。渐渐地,抖音成为人们的一个线上熟人圈。
原本用于通讯的微信不再活跃,除了一些群消息,变得一片死寂。见面时聊的家长里短,也大多来自于抖音上刷到的内容——谁家男人死了,谁家老婆改嫁,谁又发了让人觉得不舒服的视频……
这些话语里,有位常被不经意间反复提及的“网红”——南海。南海是附近地区一位卖樱桃的大姐。短视频经营得火热,也导致很多人开车去找她买樱桃,合影。
表面上,网红代表着广受人们欢迎,亦或是代表地方的一种文化符号。但南海遭遇的却是恰恰相反的评价,人们七嘴八舌之中,满是对她的鄙夷,说她“怪恶心人”,“总是骂人”,说她和几个光棍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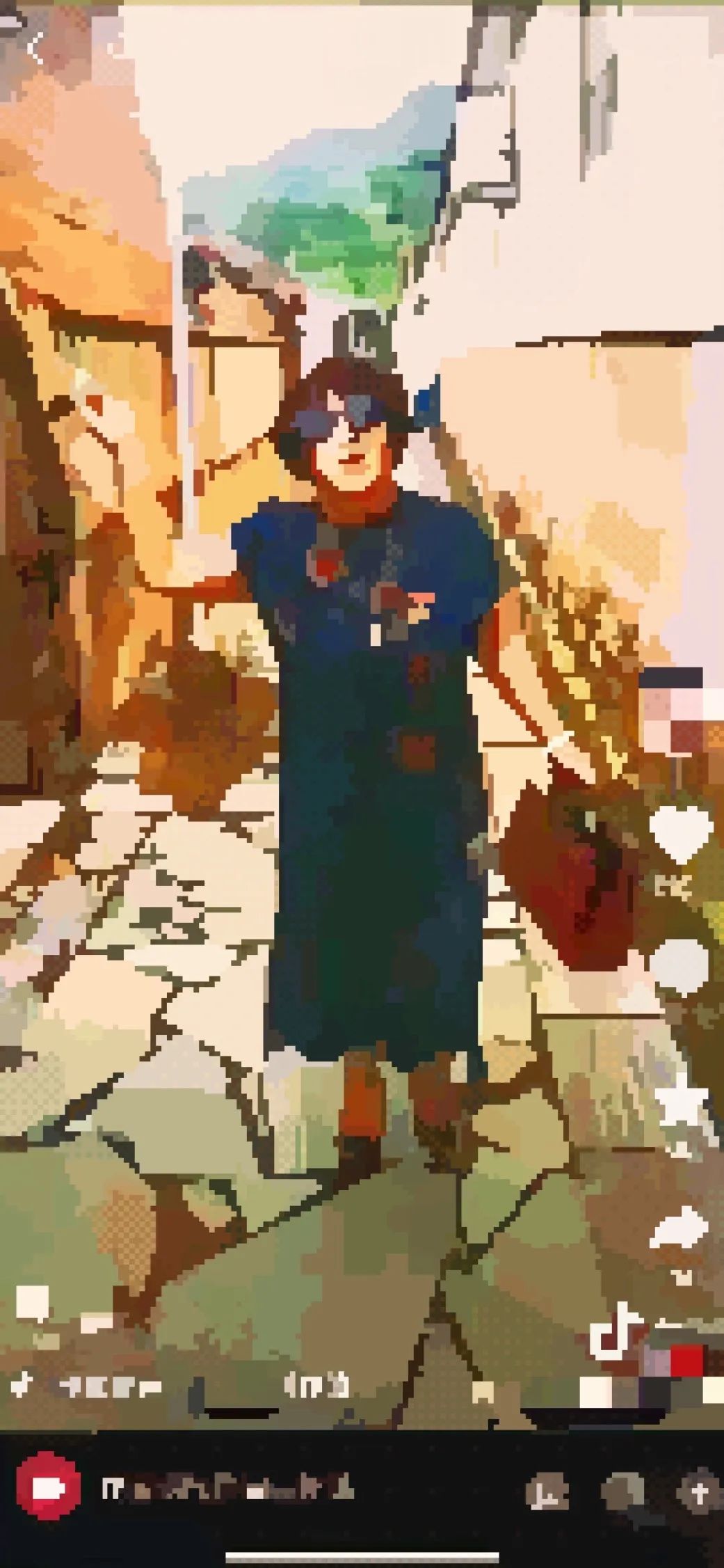
南海抖音页面 | 作者供图
短视频似乎鼓励了人们的开放表达,但一些价值取向仍非常坚固。不喜欢一些哭天抹泪的内容,“正能量”被认为才是好的、应当的、可以发的。
点开桃园的“同城”,会不断看到人们拍摄的劳动场景,配上《农民也辉煌》等表达快乐、自豪心情的歌曲;人们拍摄路边盛开的鲜花,又或者拍摄乡间的瓜果、水库边的落日、田地里的麦子……
这是自主创造出来的一种乡村景观,经过筛选的、浪漫化的乡村生活。不管实际的劳作过程有多辛苦,呈现出来的都是对劳动的赞美、对农村生活的满足。
似乎在抖音风靡之后,乡村才活灵活现起来,人们也瞬间拥有了发现美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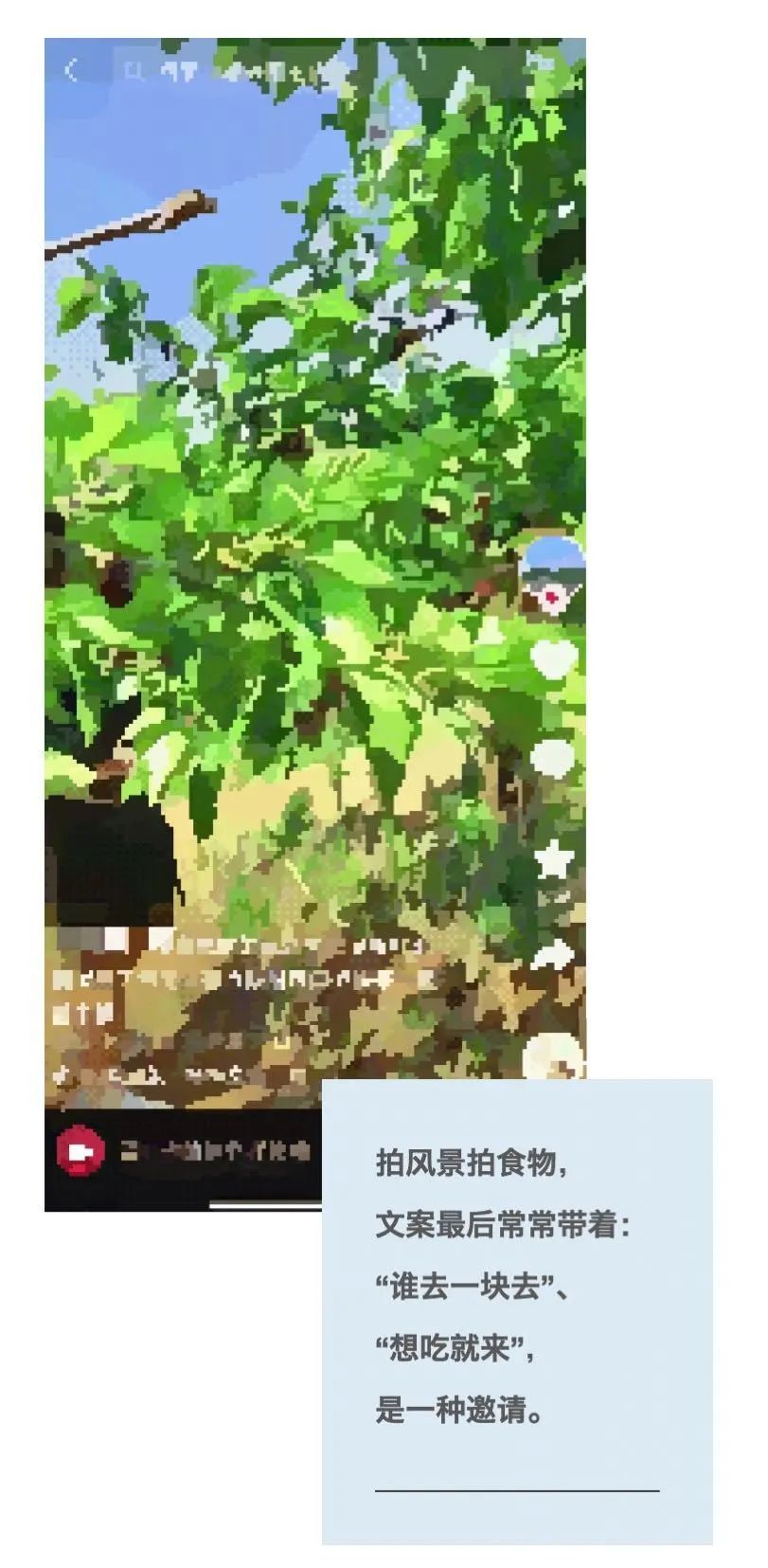
拍乡间风景的视频 | 作者供图
日常对话
历姐姐是个直来直去的人,想笑就笑想骂就骂,长长的头发垂到大腿,身材高挑,抖音里的她总是穿着各式裙子在跳舞;严姨性格温和,聊天不紧不慢,抖音里却是另一番样子,喜欢“酷帅”的舞蹈和打扮。
她们常坐在一起喝茶,聊抖音里的趣闻。
“集上卖手抓饼的‘龙哥龙嫂’很有名。”
“我让这两口子笑死了,拍得比桃园大嫂子好看。青岛小中分拍得也很好。人家弄的段子,我们自己也都爱看。”
“都一万多赞。”
“你得拍那个斧头帮舞蹈。在厨房里,在厨师忙的时候,把他拍上是最好了。”
“我之前就想过,我们这五个人,有拿勺子的,有拿刀的,有拿铲子的。”
“就是这样,扭得越厉害越好看。带着围裙,戴着厨师帽,拿刀有时候审核不过,手里可以拿着两把青菜,绝了!拎着鲅鱼也挺好的。”
“一只手拎只鸡,另一只手拎条鱼。”
“一起跳更好,不怕人多。集体的视频看重整体美,不是看某个人。”

拍村庄食物的视频 | 作者供图
历姐姐想聊天时,多喜欢去林果站——一个卖化肥、农药的农资超市,位于桃园街道中间位置,也是人们聚在一起闲聊的“据点”。
林果站大厅堆放着大袋的农资产品,左手边径直向前,便进入了老板娘的客厅。大理石地面,干净整洁、亮堂堂的。右手边是长条的沙发,紧挨着茶几,周围摆放着几个肤色的塑料板凳。茶几对面是一台液晶电视机。
落座后第一件事是连 Wi-Fi,然后才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来。手机就挨屁股旁放着。后来,历姐姐率先拿起手机来刷抖音,留下其余人闲聊。
过一会儿聊天的布局有所变化。隋姨暂时退出聊天,兀自拿起手机,“怎么潇洒怎么活”的音乐响起来,紧接着音量减弱。她已经投入到虚拟世界里,边看屏幕边咧嘴笑。
偶尔,老板娘会将话题抛给隋阿姨,她就暂时从手机中抽离,简短聊几句。在某个时刻,三人又重新回归热络聊天的状态。间歇地,她们处于公共参与中,同时也对彼此暂时的脱离熟视无睹,并不介意。

村庄远处 | 作者供图
后记:
2021 至 2022 年间,我陆续在山东诸城市辖的桃园生态经济发展区进行田野走访,范围从桃园街道一公里长的沿街房向外辐射,蔓延到附近的村子。通过目的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式,共访谈到 53 位使用短视频软件的村民,年龄介于 36-79 岁之间,使用年限则在接近一年到三年不等。
人们的对话常常有抖音的 “参与”。有时它作为一种背景音,有时作为话题的引子。有时,谈话间,对方仍会在间隙不停地向上滑动屏幕,在直播间抢福袋。
短视频像沙子一样填入乡村生活粗粝的空隙里。如果时间占比是一种评价标准,这无疑已经成为他们生活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它改造了村民的生活,村民同样也对其“驯化”、改造,构筑出平台上色彩奇特、难以忽视的一种内容形态。
(文内人名均为化名)
作者:徐七七、翁垟
编辑:翁垟、卧虫


本文来自果壳,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如有需要请联系sns@guok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