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VR 里,再次逃离戒网瘾基地
将少年时“戒网瘾”的经历做成一部游戏,既是同过往的和解,也是抗争的延续。
17 岁时,张孟泰被父母送进一家“网瘾戒除机构”。父母这么做是因为“他玩游戏”,他玩游戏是为了“逃避家庭矛盾”。同重复发生在很多家庭中的故事,困境中的父母把“问题”甩给了家庭之外那些奇奇怪怪的办法。
11 年后,张孟泰同声音艺术家 Lemon Guo 把这段经历做成一部名为《诊断》(Diagnosia)的 VR 影片。在他心目中,这是一部纪录片——观众进入他的记忆,使用他的眼睛。

VR 技术的兴起让影片和游戏的边界变得模糊,但无论被如何分类,沉浸感和互动性都让这部作品体现出区别于传统影片和传统游戏的特色。去年 11 月,它在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 (IDFA) 首映,之后多次入围影展并获奖。
30 分钟的 VR 互动讲述了一个肖申克式的故事:他如何被送入基地,如何下决心跟里面的成员串供,并使用一些小手段,最终逃离。
基地和面孔
故事从一辆车的内部开始,车外是雾蒙蒙的高速公路,副驾驶座位上的女人突然开口:“儿子,醒了?再睡会儿吧。”话到一半,被驾驶座上的男人按车喇叭打断,两个人似乎在密谋着什么。
副驾女子的配音,来自于张孟泰的母亲。当年,她和丈夫以“看心理医生”、“探望战友”的名义,把儿子骗到了这家“青少年成长基地”。到了基地门口,张孟泰试图逃跑,被几个大汉直接抬了进去。

影片中,这段经历被模糊处理:主角逐渐坠落,画面变得抽象,苏醒后就身处一间逼仄的宿舍之内。这是张孟泰无法忘记的地方,清晰地被搬进了 VR 影片之中:昏暗灯光,局促的布局,双层床、书桌、台灯,墙上涂画着一些非主流语录和脏话,以及“出去加我 QQ:XXXXX”。
桌上有张纸条,走过去拾起,光线透过铁丝网围栏的窗户照在纸条上,字迹变得清晰,上面写着,十分钟之后“你”要去见心理医生。
接下来“你”可以探索这一楼层:墙上的生活作息表、标语口号、布告栏的文字、教室里的课件……一条走廊连接着不同房间,“你”会遇见被关在这里的其他人。选中、握柄,转动门把手进入;走近,与他们交谈;选中、握柄,拾起并阅读他们的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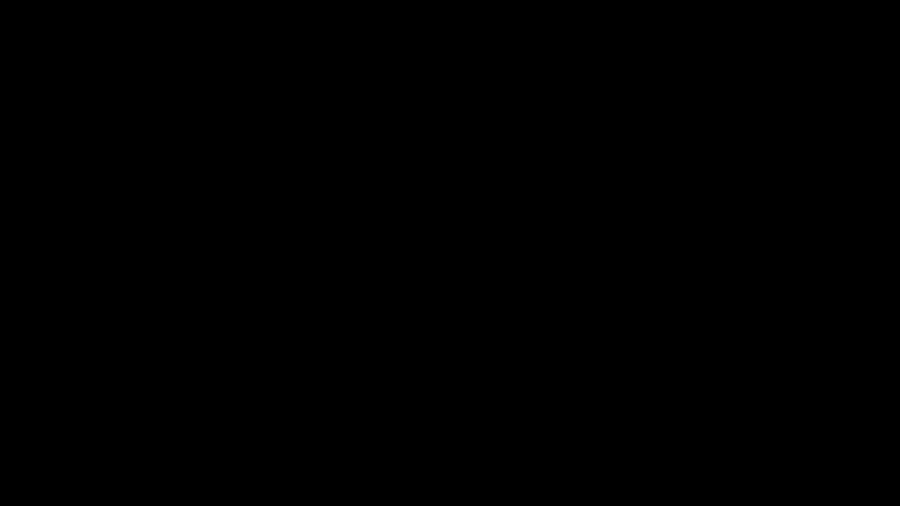
“你”很快从中拼凑出,在这个“基地”里,人们以“戒除网瘾”为由被关进来,接受军事化管理和“治疗”。
因为选择了 VR 作为载体,相比于情节,打造空间感体验变得更为重要,细节让 VR 眼镜中的“基地”显得更加真实。“那个基地的环境种种,你只要把观众放进去,他们就能感受到很多东西。” Lemon 说。
通向楼梯间的铁门,挂着“幼儿园风格”的塑料爬山虎;教室里的投影写着“精神鸦片”;窗外有媒体架着摄像机,经过筛选的学员才会去接受采访……但有些细节张孟泰仍是记不清了:父母送他进来的那条公路到底长什么样子?墙上的标语具体是怎么说的?三层的墙面上有没有刷一节绿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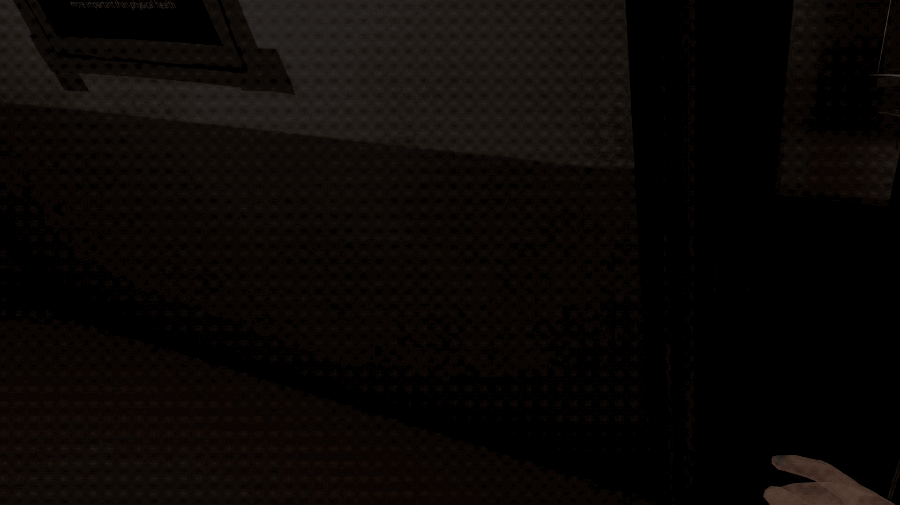
关于到底有没有这节绿漆,张孟泰反复纠结了很久。他找来当时许多新闻和纪录影像,其中,以色列导演 Shosh Shlam 2013 年的纪录片 Web Junkie (《网瘾》)是重要参考。Shlam 当年来到中国,拍下的正是 17 岁的张孟泰被囚禁的那个基地。
一些偏差是为适应 VR 这个载体而刻意制造的。走廊被设计得更短,房间更少,为的是不让观众在重复相似的门前迷失方向。
走廊串起的房间里,“你”遇到了这里的学员,他们的面部是一片动态的模糊,没有明确的五官。在 VR 场景里,人物模型需要许多面,为了减少渲染压力,这是一种技术上更简单的处理。
却又同样凑成一种隐喻。“大家被放到这里之后,都有点面目模糊。你的面目并不重要,因为一个好的孩子是什么样子,这个标准是恒定的。只要我们跟他们长得一样,就可以了。”张孟泰说。
探索楼层之后,“你”会跟着列队跑去操场,基地里早晚都有这样的操练。在这时,所有人都又有了面孔。“你”回头看见,是十几张一模一样的脸。

现实中,“教官”曾告诉张孟泰,他们卡在两个真正的军队连队中间,前面是机枪连,后面是防化连。张孟泰从没见过他们的样子;影片里,队列周围被处理成一片浓雾。雾中隐约传来训练的声号,背景音乐是做了极端的拉长和变形的《运动员进行曲》。
也有被刻意摘取掉的记忆。张孟泰的回忆里有大量暴力和语言洗脑的场景,这些在他看来都极具张力,又十足荒唐。但他选择不直接重现这种惨烈。“假设我做了个动画给你看,教官走过去抽了那个人一巴掌,这能怎么样呢?”
“重点不是那一巴掌。”他认为,“最可怕的是来自一种未知的恐怖,你知道他做的事情明显不对,却无能为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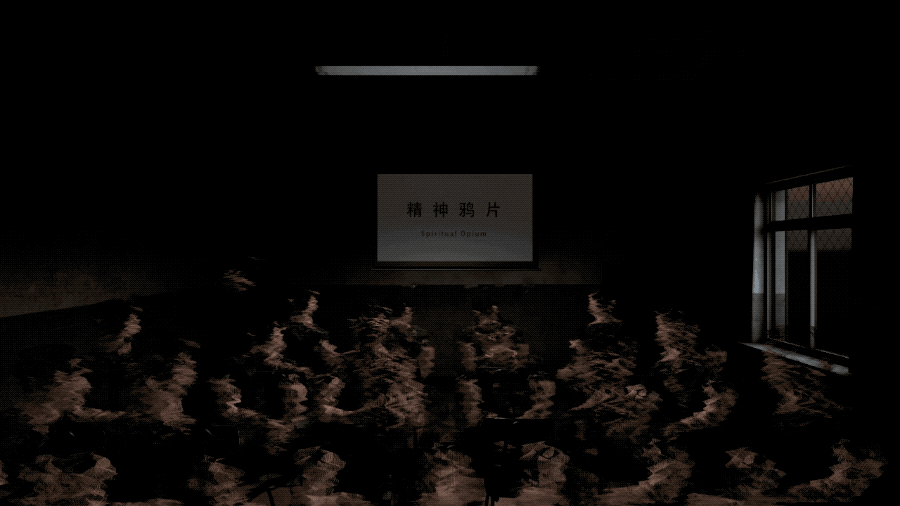
逆反、顺从、逃脱
现实中,那栋楼一共有四层,顶层住着“心理医生”和一些家长;三层一半是“基地新人”,一半是女生宿舍,中间被铁门分开;二层则是已经住了一个月以上的、“稳定”的人。
刚开始,张孟泰被分配到三层。在这里他遇到了几个人。
一个是大叔,因为网聊出轨,被妈妈和老婆联手送进来;另一个人柔柔弱弱的,天天被人喊娘娘腔;还有一个胖胖的男生,跟张孟泰年纪相仿,成天戴着个帽子。
小胖子帽子下有一块胎记,那一块长不出头发,最讨厌别人摘他帽子,谁动就跟谁急。他有些自闭,成天呆在水房里,对着镜子不停念叨:你真帅,你特别帅。
还有一个白白净净的新疆人。“那个人说话上句不接下句,做事也不符合常理。看起来根本没有办法打游戏。”他不应该在这个地方,而是真正的精神科,张孟泰想,在这里只是受欺负;小胖子也是一样,比起打游戏,可能自闭才是问题。
不久后,一位大学生进来了。他发型很新潮,像那时流行的杀马特,在 17 岁的张孟泰眼中,看起来“很厉害”。脾气也倔强,一次跟教官的对抗之后,大学生被关到走廊尽头的小黑屋子里,关了许多天。

小黑屋有个专门的名字,“森田治疗室”。这被基地视为一种重要的治疗手段,源自日本精神医学家森田正马对神经质症提出的“森田疗法”。但在这里,简单来讲,就是关禁闭。
这是影片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你”打开小黑屋的门进去,看到地上有一本日记,捡起日记会触发一段动画,“你”看到大学生坐在墙角,手上缠着绷带——现实中,刚被送进基地时,大学生曾试图自杀,把灯管砸碎了割腕,留下一道伤痕。相熟之后,他告诉了张孟泰这件事情。
“我们当时都特别理解,因为他还上着学,被送进来也不是因为游戏,而是‘早恋’。出去之后还能见到女朋友么?会不会被退学?有很多恐惧。”张孟泰清晰地记得,“而且他是成年人,没办法接受怎么突然就这样,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一两周后,张孟泰被转移到二层。这里的“训练”比三层更紧张,强度更大。他起初不愿去,但里面的人告诉他,只有经历二层才能出去。
二层氛围与三层截然不同,这里的人“集体意识很强”,还有人会跟教官打小报告。
在影片中,张孟泰为二层的回忆仅留下这样一个场景:一位“教官”被发现殴打“学员”,遭到开除。被开除那天,二层的学员都扒着窗户在哭,大喊:我们会想念你的。
这让张孟泰倍感冲击。“这个教官脾气时好时不好,但最终还是一个施暴者,他现在走了,我们为什么还要送别他?”
搬到二层不久,基地召开了一个“亲子见面会”。形式有些像军训阅兵,学员要在家长面前走正步、喊口号、唱歌。“意思是我们作为一个产品,现在 ok 了,性能还不错,让家长来看一下。”
人群中,张孟泰发现了自己的父母。他赶紧上前求救,想让父母把自己“从这个可怕的地方弄出去”。母亲满口答应,但随后,他就被一个教官“骗上楼”,关进一个空房间里。门被反锁上了。

从那一刻起,他下定了决心。“好,那大家就开始演吧,你想要什么样子我就装成什么样子。”
影片通过对话和日记,讲述了这条隐秘的故事线。现实中,张孟泰和大学生发现,心理医生会安排他们互相盯着对方,打小报告。于是他们开始合作,互相串供,帮助彼此装出“好孩子”的样子。
策略成功了,两个人只呆了一个月左右就离开了基地。相比之下,这里的大多数学员都要呆三到六个月。每个人的学费约一万块钱一个月,几乎是当时中国城镇居民一整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共同的沉默
进入基地之前,张孟泰打游戏是为了逃避家庭中父母长期的矛盾争吵;从基地出来之后,矛盾并没有消失,他还“变得更愤怒了”。
“被治疗”后发生这种变化,张孟泰并不是唯一。常有家长跑到网上去问:把孩子送进去,未来会不会被报复?原来家长也会害怕,他第一次意识到。
时间逐渐冲淡了这件事在家里的痕迹。他与父母都几乎心照不宣地决口不提,“毕竟精神疾病在中国总是一个不太好的说法”。
现在回想,他发现,当时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相似的氛围中。
中国很早就已经出现类似网瘾的说法,“那时还不叫网瘾,叫沉迷、迷恋,好像程度还挺浅的。”到 2002 年,出现了蓝极速网吧纵火案, 25 人在事件中死亡,此后政府对网吧的管制大大加强,“打游戏有一天会发展为犯罪,成了一种很普遍的认知”。
到 2007 年,“这就进化成了一种疾病,可以被治疗”。

来源:东方 IC
刚从“基地”出来时,张孟泰偷偷搜索过基地的背景。“说当时中国(治疗网瘾)有三大门派,一个是吃药的,一个是电击的,一个是谈话的。”他所在基地的创始人陶然就是第一种。
影片中能看到走廊里送药的铁皮推车,经过时,一旁的学员会提醒“你”,不要把药吞下去。基地流传着未经证实的说法,吃了这个药会失去性功能。新来的学员会被“老人”教导,如何将药丸藏在喉咙管里逃过检查,再去厕所扣嗓子眼吐出来。
“电击的”一派指的则是杨永信。2008 年,张孟泰离开基地不久,网瘾治疗在中国经历了巨大的舆论反转,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杨永信所代表的电击疗法遭到质疑。2009 年,央视《新闻调查》报道杨永信使用违禁的电击设备,同年,卫生部叫停电刺激(或电休克)治疗“网瘾”技术的临床应用。
“我被送进去那一年,媒体漫天遍地都在渲染网瘾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对当时的社会状态,张孟泰大致是这样的感受。“而后来,不光是我闭口不谈,可能有不少人都希望大家别再谈论这个事情了。”
他印象中,2009 年开始,与网瘾相关的报道数量骤减。这个话题波澜壮阔而起,又被轻描淡写地带过了。
当张孟泰再次想起深究这件事,并开始创作 VR 内容时,已经是 2018 年。
在影片中的最后一个场景,“你”会来到 2018 年张孟泰开始制作游戏时居住的那个房间。整个房间被做成一个文献资料库,几年来张孟泰和 Lemon 收集的一切“网瘾”资料都在这里。电脑上播放着对基地创始人陶然的采访,大量的照片与论文,像侦探破案的线索一样被贴在墙上——影片中严丝合缝地复制了现实中房间里的布局,走进“你”可以拿起照片,在 VR 空间里阅读墙壁上的文献。

从这些庞杂的资料中,“你”和张孟泰才“一起”了解到, 2009 年之后发生了什么。
都有病
2010 年,陶然作为第一作者的《网络成瘾诊断标准的建议》在英国成瘾研究学会(SSA)的杂志 Addiction 上发表,在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论文界定了网络成瘾的病程标准:平均每日连续(非工作)使用网络时间至少六小时,持续至少三个月。
该标准 2008 年就已经在国内发表。根据当时的报道,陶然所带领的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为国内第一家网络成瘾诊疗基地,该基地抽取 1300 余例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进行临床跟踪研究,制定了这个诊断标准。(论文中实际提到的为 500 多例)
在一篇封面文章中,北京科技报旗下的《科技生活》杂志回顾,在国内最初发布后,《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饱受质疑,“陶然只得谋求国外学术界的认可”。继而出现了 Addiction 上的英文版本。
在国外,这个理论同样卷入许多论辩和争议,但经此一役,中国对网瘾的认定和治疗瞬时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
2010 年,以色列导演 Shosh Shlam 来到中国,拜访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拍摄了纪录片 Web Junkie 。影片中表示,中国是全世界第一个承认网瘾的国家。片子引发大量关注和媒体讨论。上映一年之后,张孟泰住过的那个基地突然搬家。
学术层面,由于样本数量大且有丰富的临床研究,陶然的诊断标准很快成为网瘾话题中被广泛引用的理论,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相关讨论的进程。
2009 年,《自然》杂志报道了陶然的实践。文章提及,当时,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PA)正考虑是否应将“网瘾”纳入 DSM-V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但讨论尚未达成共识;几年后,事态就出现变化,网络成瘾以 “Gaming Disorder” (游戏障碍)的名字出现在 DSM-V 第三节。
虽然这仅意味着,APA 学会认为, GD 是否为一种精神疾病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和数据积累。但这仍被视为陶然获得国际认可的证明。在当时的报道中,被广泛误用的论调是, DSM-V “全盘采纳了陶然制定的《标准》”。(DSM-V 原文为:对该标准的描述改编自中国的一项研究)
更具决定性的瞬间出现在 2019 年,世界卫生组织投票认定 GD 为一种行为成瘾,纳入 ICD-11(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
但这个话题远并没有因此尘埃落定。仍有许多人认为,并没有足够的研究和科学证据来支持这种认定;也有人担心,这会让网络使用和电子游戏被整体认定为“负面的”、“病态的”。
陶然的治疗理念一直以来也争议不断。《科技生活》写道,“有人骂他是‘疯子’‘黑监狱长’,因为他将游戏成瘾定性成一种病,并在封闭大院里像集中营一样培训和教化‘网瘾学员’。”
通过自己的 VR 作品,张孟泰试图通过亲身经历提出质疑。“在西方世界看来,陶然的研究似乎有一个很扎实的基础。但问题是,我们并没有告知会被拿来做实验,基地里很多人都是被骗进来,甚至被家长用安眠药弄进来的。”
“很多人被送进来不是因为打游戏,出去也不是因为‘被治愈了’。”他说道,“我们都是在表演。”

“网络鸦片”回归
创作《诊断》的过程中,让张孟泰和 Lemon 意外的是,“网瘾”这个似乎早已成为过去时的话题,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电子海洛因的说法又回来了。”
2021 年,《经济参考报》一篇《“精神鸦片”竟长成数千亿产业》引爆网络,游戏相关的上市公司股价应声暴跌;同年八月,“最严未成年防沉迷”出台,规定企业一周仅可给未成年人提供 3 小时服务,即周五、六、日晚上八点到九点。
网瘾戒除机构则从未真正消失。2019 年,《中国青年报》报道,过去 16 年,像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这样的机构在国内从一家增至二三百家。
今年,世卫组织的 ICD-11 正式生效。
“他(陶然)在媒体上会反复讲一些夸张的案例,比如有些小孩为了不用离开座位,在网吧穿着尿布打游戏;他还会把那些孩子形容成冬眠的动物,冬天穿着羽绒服去网吧,到春天才出来。” Lemon 表示。这些故事广泛流传,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诊断》作为 VR 影片在纽约展映时,一位影评人表示,连他也知道陶然著名的“尿布故事”。
影片中最后一个场景的资料墙上,贴有一份报道,是关于科学界的可复制性危机。近年来越来越多实验发现,许多已发表的研究无法被复制和验证,此现象在心理学领域尤其突出。

正式制作 VR 作品之前,张孟泰花了好几个月,写了一个两万多字的回忆录。动笔之前,他觉得,这可能是个挺悲惨的故事;书写过程中发现,似乎悲惨里也透露着一些普通人小小伎俩,来对待自己无法抵抗的、系统性的力量。
“做这个片子也是希望大家能更了解,他们在治疗的到底是什么,以及那些所谓的有网瘾的,没有面目的人,他们是怎样的人。”张孟泰说。
“他们的生活中,都面临了一些自己没办法解决的事情。我们可能更需要关注这些问题,而不是给他们扣上一个帽子。”

(文内未标注动图与图片均来源于受访者)
参考文献
作者:翁垟
编辑:卧虫

本文来自果壳,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如有需要请联系sns@guok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