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扒窃曾是一项骄傲的“传统”,它独特且富有戏剧性,扒窃者甚至发展出一整套复杂的“行业话语”进行沟通联系。但这样的日子似乎结束了,据《纽约时报》报道,1990年纽约共有23068件扒窃案,带来近千万美元的损失,5年后这个数字降至一半。今天,纽约警察局甚至都没有单独记录扒窃案的数量。
去年,一个纽约地铁警察称现在只有中年人、甚至更老的扒手还在列车上“工作”,数量也寥寥无几。“这一行里已经没有年轻人了。”这位警员说:“它正在走向衰败。”正如德州州立大学的犯罪学家马库斯•费尔森(Marcus Felson)所说,扒窃是“一门正在消失的艺术”。
列车扒窃的衰落挺让人意外的。其实地铁一直是扒手们最喜爱的猎场,他们结成团伙或单独行动。扒窃团伙分工明确:“神偷”专挑有钱人,“钱包党”只奔着钱袋去,而“酒鬼党”名声不太好,因为他们专找已经不省人事的醉汉。
理查德•希诺特(Richard Sinnott)是20世纪70和80年代在纽约交通系统工作的警员,回忆起那些“技术派”仍佩服不已,他们用食指和中指从乘客口袋里夹取纸币和钢镚儿,这里几毛,那里几块。“他们不贪心,所以也从没被逮到过。”希诺特说。积少成多,一趟地铁就能收获400块,到冬天便足够去佛罗里达玩赛马。而其他城市扒手则四处苦练技艺,“一旦技术足够好,他们就跑来纽约”。希诺特有点骄傲:“我们的地铁里汇集了扒窃界得精英。”这也使得扒窃在纽约猖獗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现金少,技术难
关于扒窃的消失专家给出了几种解释:人们随身携带现金越来越少,信用卡或借记卡的安全性增强,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数百年延续下来的扒窃师徒制度正在面临崩溃。就像《雾都孤儿》(Oliver Twist)中的情节那样,经验丰富的老扒手吸收年轻孩子入伙,传授技艺。但随着法律对扒窃的惩罚措施逐渐严厉(在一些州,无论偷盗数额大小,扒窃都会被定为重罪),以及对热点地区更严密的监管,促使了这个制度的瓦解。
与美国不同,在欧洲,扒窃并不是警方优先关注的问题。自从2007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国加入欧盟后,来自这两个扒窃之国的高手们能自由穿行于欧洲各国,如鱼得水地在巴塞罗那、罗马和布拉格这样热门旅游地区发展他们的事业。
鲍伯•阿诺(Bob Arno)是一位勇于卧底的犯罪学家。为了掌握最新盗窃技术,他四处旅行,假扮受害者,帮助执法部门抓住罪犯。阿诺发现,在欧洲,优秀的窃贼平均在22-35岁。但美国这个年龄段的扒手已经绝迹了,还有一些因为被逮捕次数太多以至于警察很容易追踪和抓到他们。

团伙扒窃的一种。图:HowstuffWorks
不过就算神偷们再努力,现今的美国孩子是否愿意花费大量时间去学习扒窃技巧也很难讲。“扒窃是个细致活儿。”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犯罪学家杰•阿尔班斯(Jay Albenese)说:“这需要技巧、细心、耐性,做事聪明同时要有计划性,而这些美国年轻人是不具备的。”
他认为,扒窃的消失更像是一个广义文化的反映。由于枪支在美国并不管制,所以那些胆子大的人大可去持枪抢劫(尽管美国对持枪抢劫的惩罚更严厉)。而那些不那么暴力的人可以靠着在地铁抢手机谋生,这可比偷来的信用卡更容易变成钱。
虽然信用卡诈骗和身份窃取获利更多,但技术要求太高,也丝毫不迷人(黑客多迷人啊,看来美国人民不粉技术宅)。在拥挤的地铁车厢斗智斗勇是一回事,而作为一个匿名黑客窃取账户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天下真将无“贼”?
怀念扒窃很愚蠢吗?也许是,但可以理解。扒手在美国文化中一直是个“有范儿”的职业,如果身怀绝技,那在旧时的美国甚至是个不错的职业。
在电影中,扒手,或者说“神偷”们也一直是传奇搬的存在:他们在袖子挂有铃铛的假人身上苦练如何窃取到钱包而不发出声音。在2001年的电影《十一罗汉》(Ocean's Eleven)中,各路明星扮演的角色机智并且身怀绝技。马特•达蒙(Matt Damon)的角色是个扒窃高手,但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扮演的Danny Ocean却能偷走他刚到手的钱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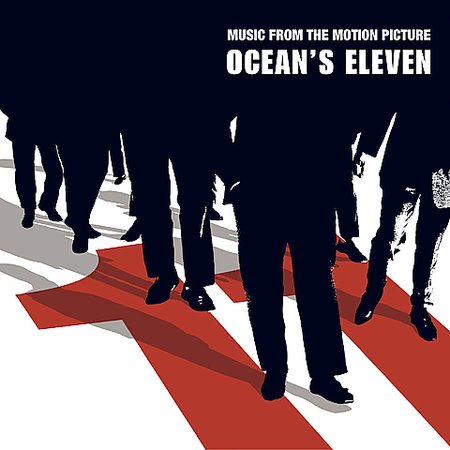
电影《十一罗汉》海报。
类似例子还有很多。比如1973年的《妙手空空大行动》(Harry in Your Pocket)就成功塑造了经典扒手性感的一面,同时带着深深的怀旧之情。主角哈利的技术一丝不苟,着装无可挑剔,旅行只住最好的酒店。但时代变了,艰难的日子也随之而来,哈利的老搭档凯西慢慢失去市场。他陷入迷茫,开始怀念过去的好时光。“技术什么的都是扯淡了,”他向一个有前途的新扒手抱怨:“现在年轻人哪会技术,他们没耐性无纪律,也不愿花时间见去学习,只能打昏穷老太太抢他们的钱包,这是绝对不行的。”
与哈利相似,在冯小刚的电影《天下无贼》中,葛优扮演的神偷黎叔也表达了自己对抢劫者的不屑,在这趟火车上,各路神偷大展身手,好不帅气。而在英剧《飞天大盗》(Hustle)中,几位主角虽然以长期骗局为主,但他们每人都仍然具有高超的扒窃技巧,并且每次都需要以此来“赚取”本钱。
尽管时过境迁,但电影依然说中了事实。虽然钱包仍然会不翼而飞,但一个事物彻底消失毕竟需要时间。在1960年 《科技新时代》的一篇讲述扒手的文章中,那些老扒手就预言年轻一代迟早会让这门技术荒废掉。“老扒手们正相继死去,而年轻人缺乏努力和进取心去学习这些‘技巧’”。
目前,还有少数扒手存在于美国的城市以及老式巡回剧团中,根据犯罪学家阿诺的说法,碰上大型体育比赛和一些“有宽松的司法环境和对反扒不在行的警察”的小城镇,只要不至于发展为欺诈或重罪,他们还能干上一段,但貌似也走不了多远。想象一下,当昔日风光的扒手,佝偻着最后一次走在地铁站台上,颤抖着拾起废弃的空钱包时,这一切也就结束了。
20世纪40年代,旧上海滩的扒窃党也曾发展壮大,这一时期的扒窃党有时着实“日进斗金”,真是辉煌年代。不过正如黎叔所说,“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也许美国的趋势和现状不太会在全球重现,但如果扒窃真的消失了,街上都是劫匪的话,那确实挺伤感的。
本文编译自 Slate:The Lost Art of Pickpocketing ,有修改
